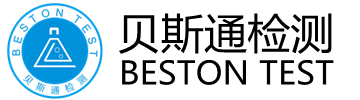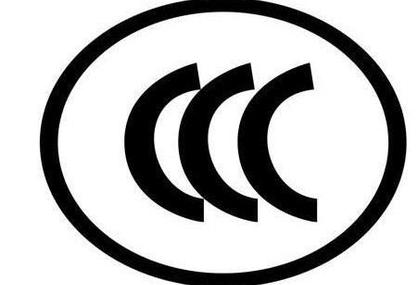[摘要]“每年工资奖金都扣,红黄牌也扣钱,但我也不在乎。第一我没想把对手踢坏或者踢折,我完全就是为了球队利益。我是脏,我不是杀人。
来源:知名媒体人孙雷的谈话节目《对雷说》
“合同到年底结束,明年我不会再继续了。”
聊了没几分钟,周挺的告别宣言就顺嘴说了出来,打了我个措手不及。这样的段落应该煽情煽到一定程度才开始,万不能这样草草开始草草结束的。
“我踢了24年了,老天够眷顾我的了,我够幸运的了。”
画面里的周挺,在大连某个多年前他就包下的农场里,确切地说,是某间连摆手机的桌子都没有的房间里。以至于他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,一直用手持的方式保持视频连线,从没有抱怨过。
周挺参加《对雷说》亲承将在赛季结束后退役
我愣神,觉得我一上来聊退役太过诡异,又觉得他就此说出退役太过随意,只好把话题引回到许多年以前。
1997年,周挺离开大连万达梯队,加盟深圳金鹏,这支球队,就是后来的云南红塔。当时周挺只有18岁,他怕是想不到,再回家时,已是20年之后的事儿。
这20年间,周挺给人留下的印象很简单:“硬”、“脏”。
“硬”指的是他的比赛态度,没躲过刀山球,没怕过面对面。“脏”,指的是他拿到红黄牌的纪录。
“我从6、7岁开始踢球,到我踢职业联赛,你想想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年?一两年就把过去教练灌输给你的东西改变了?不可能的。”周挺说。
周挺出生于1979年,他开始踢球的时代,是体制足球的末代。那个年代,每个踢出来的人都有一手绝活,每个教练也都会传授很多技巧。
“以前像我们这个年龄踢球的,大连队、辽宁队、八一队,都踢球比较凶,都比较脏,大家都是这样。从青少年踢到到一线队,年龄段每个队三十多个人,就剩五六个人能踢到职业联赛。一点点淘汰,剩下的就是这些人。我们这些人的理念就是这样,每个队大家都是这么踢的,所以没觉得怎么样,不光是我们队的教练这样,辽宁队教练也是这样,八一队教练也是这样,大家都是这么教的。”
“教教我呗?”我问。周挺一笑:“下次当面教吧。”配合着他的笑容,我读出了威吓的味道。而威吓,便是他的技巧。
“巅峰”时期,周挺只要上场就会拿黄牌,当时两场一停,周挺就踢两轮歇一轮。
“每年工资奖金都扣,红黄牌也扣钱,但我也不在乎。第一我没想把对手踢坏或者踢折,我完全就是为了球队利益。我是脏,我不是杀人。所以我觉得也没必要上纲上线,我就是个犯规,红牌是球队受累了,我也接受惩罚,确实也是错,我也都认。但是你要听人家一说,你就不踢了,那还咋继续,还能踢到41岁吗?”
“你得扛住压力。”周挺说。
“脏”的踢法,让周挺挨了许多骂。渐渐的,骂的人变多了,开始是对手,后来是自己人。俱乐部老板开始找周挺的爱人谈话,希望周挺收一收脾气。有点儿像小学班主任找家长的感觉,渐渐的,周挺从“我一个人的时候从来没怵过”,开始觉得“有点儿对不起家人。”
他开始把自己的性格和自己做的事儿分割开,也渐渐的把自己的初衷和最终的结果分割开。突然他明白了个简单的道理:“我做出这件事没有一点好的效果,让大家都跟着受牵连,我还总是去做,有点太没良心了。”
早早离家,在外边的世界闯荡许多年的周挺,这才开始改变。坚持了许多年的认知,在家人和责任面前,渐渐融化了。
仔细想来,周挺的“脏”,给自己带来了什么?
“我从来没要求过俱乐部说得给我1+1合同或者是两年合同,我真的从来没要求过。我从33岁在国安的时候,踢一年签一年。包括当时回大连一方也是,不管我出场率多高,我都是一年一签。我觉得一个是我得对要我的俱乐部负责,另一个我得对我自己负责。我有状态我才能继续,不能作为一个老球员,三十多岁了让人说骗人钱或者是养老,这样我觉得没意思。所以谈不上坚持,2017年回大连我还是去试训,我回来那年37岁,当时在国安的时候,扎切罗尼走了以后,我还踢了十几场。”
2017年,周挺回到大连,加盟大连一方队。当时的主帅卡罗觉得周挺年龄太大,要求他先试训,周挺虽然觉得“这相当于骂人”,但年龄毕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,于是还是接受了。周挺飞到了昆明,在高原和球队汇合,他记得下午3点多下的飞机,4点多就和球队合练了。
三天之后,教练通知周挺和俱乐部签约,试训通过了。
周挺是个极度要强的人。
而他极度要强那一年,是在2011年。要强的点,是他为了“有点儿良心”,努力不吃牌。那一年,联赛加足协杯,周挺只吃了3张黄牌,并打满了全年的比赛。
“一个赛季我全都踢满了,包括足协杯,全踢满了,一分钟没差。我觉得那一年确实是我整个职业生涯可能是最完整的一年。三十多场比赛,谁能想象到三十多岁……你不说受不受伤吧,我是踢后卫的,拿了3张黄牌,你想想多难,这是最难的,我也不是守门员。”
你看,一个极度要强的人,连他要强的方式,都这么与众不同。
正聊着的天,被打断了。
周挺侧目,双眉紧皱:“你俩能不能出去?快点,要不我生气了。”原来是两个儿子破门而入,求父爱来了。待他们说完,孩子出门,我便开始吐槽周挺:“真吓人,我看着都害怕。”
周挺一脸无奈:“他俩不害怕,一点儿都不害怕,你看这一会儿进来多少次了。”
我说:“你这算从小给孩子练胆儿,等他们再大点儿给他们看看你踢球时候的集锦,保准以后出去见谁都不害怕。”
周挺还没决定未来的规划。平时教两个孩子踢踢球,还没到决定是不是踢专业的时候,但他想多学学,起码需要教自己的孩子。
“你会把当年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吗?”我有点儿挑事儿地问。
“我会把最好的给他们,我也得去学习,然后看看把好的给他,不是把我的给他。我不都是好的,有很多都是不好的,所以我不知道能给他的是什么。我想如果有条件,世界我不敢说,最起码亚洲觉得好的这些东西,再加上我的经验,尽量的让他们接受,结合实际结合理论,去教给他们。”
周挺说。
我又是一愣,下意识问道:“你的那部分,跟着你就退役就完了?”
周挺说:“那肯定,我肯定已经过时了,别说到他们那儿,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,已经过时了。”
我突然想起来,早在聊天的刚开始,周挺就说过退役的事儿了。“合同到年底结束,明年我不会再继续了。”
“你…不想办个退役仪式么?”我问。
“不办了,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办的,我也没有什么成就,只不过就是比其他队员踢比赛多一点,职业寿命长一点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办的,平平静静的安全降落了就完事了。”
我觉得刚才的一拳挥空了,于是继续追问:“你不想享受一个在大家面前哭一次的机会吗?”
“可能真是12月31号退役那天,我想可能会落泪。但是我觉得在哪儿落都一样,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出我搞一个退役仪式的理由。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理由搞一个退役,我也不是什么成功人士,马上要换工作,换个工种,一个工作结束了,新的生活要开始,其实就这么简单,没有必要搞一个仪式,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。”周挺说。
我才反应过来,周挺宣布的除了退役时间之外,还有他的平静。如同在孩子面前宣布他的“过时”一样,这一关,他早就过了。
可我仍然不依不饶,继续问:“到退役那一天的时候,你想跟自己说什么?”
这次周挺终于犹豫了一下,然后说:“我现在想,这个句号现在画了一大半,画了98%了,现在就差那一点点。当我把这剩下的一点画上,我就觉得是一个句号,很平稳很圆满,就结束了。”
我脑子里冒出了个名字,唤作裘千仞,画面满是他已被剃度在一灯大师旁的场景,可就是想不起那个叫做“慈恩”的法名。
眼下的周挺,在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C队,他保持着75公斤的体重,和每周足以保持状态的训练。我想打个圆场,也是自己的真实想法:“如果有机会,等到第二阶段的时候,哪怕再有那么一两场,谁知道?”
他的回答是:
“其实我还是想,如果你第二阶段见到我,我又回到赛场,我们俱乐部肯定是在保级组。我还是希望我们球队这些年轻人,真正的能达到这个要求,跟俱乐部老板的想法能一致。我不能说是咱们去争冠组,最起码在保级组也是稳稳当当的这种。毕竟我要是去了,那肯定是不是太好的结果,咱们就不说那不吉利的话。我还是希望俱乐部平平稳稳的,然后我也平平稳稳的,度过这4个月。”
那个中国足坛历史上,传说级的“恶人”要退役了,他其实并没有变,只是把自己的执着,换了个方向。
哦,对了。
还有一句,我问了周挺职业生涯的遗憾。
“在国安只拿了一个联赛冠军,我觉得太少了……”
(完)